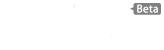少女和梦渡
汐罹 发表在 4650 天前
1.
十月的黑夜总是花掉我大量煤黑色和墨绿色的颜料,客厅里的风铃被从开了半边窗户外吹进的风摇晃得叮咚作响。在我准备拧开第二瓶墨绿色颜料的时候,珍和终于回来,寒冷的风灌进房里,门被关上,我猜想是风吹的,因为动静很大。
姐。她叫我,声音有些疲惫。
嗯,外面很冷吧,风那么大。因为天气冷的缘故,那瓶颜料被我拧了很久才妥协般被我打开,我没有停下手中的活,甚至没有望向她。直到许久之后没听见她的肯定回答,我才疑惑扭头去看她,见她仰面躺在冰凉的地上,我慌忙跑过去。弥漫大雾的眼睛没有焦距地望着天花板,鼻子不停地翕动着。
靠在我肩上吧。我把她从客厅拉回她的卧房,让她的头抵着我的肩。才发现手掌上有多黑色的颜料,它们凝固起来,像一块干涸的田地。我的心便是如此。随后我的肩上湿润的一片,卧房里没有开灯,黑暗中我看不到她的脸。以至于我有些不安,她开始从啜泣变成嚎啕大哭,一时间我找不到任何语言去安慰她,我总是这样不善于去安慰人,那些温柔的语言总是躲藏的细腻的心里。我只是搂住她,轻拍着她的背。帮她擦拭眼泪。手上黑色的颜料遇到水开始融化,我起身想去洗净着肮脏的手,她反抓住我的手,颜料弄脏了她的手,侵染了她黑色的头发,与黑夜融合在一起。
我们从来都不能选择自己要爱上一个怎样的人,就像我经常会想,我与珍和会和一个怎样的人相爱,未果。这是我们不能控制的。
爱情有时荒诞,可仍有人去尝试,并且死而无憾。
2.
2009年小年夜,那时北京下着大雪,有些温暖并且酥软,我没有时间欣赏这不寻常,甚至没有觉得这雪有多么不寻常,地上,房檐上都是白色的雪,放眼望去,一片平川。没被雪覆盖住的地方就成为了那一带显眼的标记。我在地铁站等地铁。没有坐过地铁的时候我以为地铁是不用等的,对于等待我过于烦躁,却总是心安理得地让人家等待。工作了五年,坐了五年的的地铁,等了五年的地铁。和北京繁密的上班族一起在阴暗的远离地面吵杂的站台。即使这里阴暗,也会觉得温暖。我才发现原来“习惯”这个词,也可以子这个时候用在我身上。
等到地铁哐当驶来时,我开始惘然。我将起身到医院。
一个小时前,接到母亲的电话,说父亲阑尾炎需要做场手术,还在公司加班的我慌忙收拾东西到珍和的学校,那时她在补课,高三的学习让她们在过年之际也不能得当全身心的放松,而老师告诉我她没来学校,于是怀着愤怒和忐忑走出了学校。只是现下最担心的时父亲,他苦了大半生。尽管对我们严厉,我是心疼他的。这么想着,眼泪突然就涌了出来,车厢里陌生,陌生,一切都是陌生,这些陌生人看着我裸露出的心情,漠然地望着我,我羞愧地擦拭,像身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般羞愧。幸好已经到站,我狼狈地从站台跑出来。这样狼狈地跑了几分钟,终于到了医院。
雪白的墙,还有穿着老旧得白森森的白大褂医生,白色的棉签,白色的纱布。进了医院,我才知道原来有这样一处地方,及时和外部的世界一样雪白,但是没有风霜雨雪。我整理好凌乱的头发和衣服,站上电梯。
九楼,907房,402床。我已经确定好位置。
电梯里还有一个人,一个女人。她没有什么表情,看不出是欣喜或是忧伤,或者说,她并没有遇到什么可以让她高兴或是难过,又或者,她已经长期处于某种状态下,感情在意麻木,不过我更愿意相信前者。巧的是,她去的也是九楼。
我在拐弯过去的第三个房间找到额他们,出乎意料的是珍和也在,她装着一盆热水,给父亲擦手,鼻子被风吹得发红,大概刚来不久,母亲在削苹果,病友们在漫长的治疗中找寻消遣的方法。他们在我进来的时候齐刷刷看着我,为了不沉浸在尴尬中,我借口上厕所,转身的时候发现刚才在电梯里遇见的女人,我几乎是踏出电梯的门就把她给忘记,之前也没觉得还能遇见她。
医院这么大。
她在给404床的一个短发女孩打针,女孩面色有些潮红,嘴唇有些苍白,针管轻柔地送入女孩的手背,那只手背已经被打得淤青,女人的眼泪滚了出来,我终于看到了她的表情。而哪个女孩却在沉睡。
那时的我们在路途上盲目地行走着,不知道牵引不明白宽容。
父亲在除夕那夜就出院回家,他执意要到家中过年。医生确认着不会影响她的治疗后,母亲才喜滋滋地给他办了出院手续。父亲那那一年回了家。而那场大雪,从那一年下到了这一年。
大年初一。街道上荒芜得让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忙碌的节日里显得特别多余,多余到每个人都在亲戚家拜年的时候,我还在带着珍和在回家路上漫无目的地行走——刚到公司交画稿。因为父亲生病,亲戚们都跑来北京拜年,所以即使在呆在家里,忙忙碌碌的也只是那些亲戚。
下午三点空旷的马路透着一些荒凉,雪暂时停了,但仍旧湿润,积雪很厚,脚一浅一深地踩下去发出咔吱咔吱的声音。此刻的城市没有往日的车马喧嚣,亦无人潮涌动,单只的行人看起来越发的冷清,庞大并且寂寞。
倒是珍和,回家路上遇见了几个同学,她把身上带着的贺卡送给了她们,说笑着打闹了会儿,突然觉得自己是空落世间的过路者,格格不入。
呼吸着冰冷的空气,致使鼻腔有些疼痛,不过伴随这种疼痛而来的,是冬天寒冷的熟悉,这种感觉总能让我觉得见到一个久违的朋友那般亲切。身心就这样愉快起来。
在经过医院的时候,有个短发女孩叫住了珍和,她有些紧张和窘迫,珍和也没有从口袋里拿贺卡送她。她只是对着女孩微笑,好像两个刚认识的朋友。
她说,过年好。女孩也微笑,过年好。
无异于常的对话或举动总让我好奇心萌动,我打量起这个女孩,她穿着一条黑色的牛仔裤,可以用孱弱来形容她,短发前的刘海服服帖帖地付在额前,樱桃一样的眼睛,冷风灌进她单薄的身体,因为紧张而咬得发红的嘴唇不停地打着颤,她努力控制着自己不这样失态,看出她在我面前有些拘谨,不过是个可爱的女孩。
在下好这个结论后,女孩发现我在注视她,于是对我笑笑叫姐姐。我给了她一个微笑,这是惯性,我习惯用微笑敷衍陌生人。
你和爸妈说说,我和朋友去玩会儿,晚饭前回家。珍和拉住女孩的手,对我挥挥手示意我快回家去。
嗯。我转过身,我知道她没听见我的回答,因为她们已经走很远。
有时候我们会想不起来,一些长相熟悉的人是在哪里与他们邂逅,那个女孩,也是似乎很久之前就在哪里见过,只是那个点总是想不到,有时候人们会突然忘记一件事,努力回想却想不起来时,会变的焦躁不安,随后又会想出点什么事寻求慰藉,然后心情又变得好起来。因为到了家里看见一群人忙碌的身影和满屋的清香,烦恼的事情早已抛掷脑后。
正月十六,吃过晚饭,带着小外甥和一群说不出辈分的孩子到楼顶放烟火。大概所有提及烟火的形容,都是转瞬即逝。曾画过一幅浩大的烟火,看久了,就不觉得有多新鲜。孩子们拿着从大人荷包里“变”出来的漂亮烟火,他们兴奋地点燃。或许是过了那种年龄,觉得这个年和平常的日子无异,过不过年,日子都得照样过下去,只是孩子们不容易满足,即使让他们在三伏天拥有那些绚烂的烟火,他们还是觉得在寒冷的冬季玩会比较又气氛。
天气的问题吧。我把手插进风衣的口袋,才发现手机没在口袋,围巾上竖立的绒毛扫着鼻子有些痒,低着头看地上厚实的积雪,我的心和它们一样充实着。被孩子们点燃的烟火散发出黄色的光芒。他们欢笑着踩在雪地上,我对着那散放在冬夜里黄色的光芒吐了一口热气,吐团黄色的气体很快消逝在也空中。
带这些孩很无聊吧。珍和伸手递给我手机,我接过来,下意识看看屏幕,有六个公司的未接电话。本来不想上来吹冷风的,看你手机震个不停,怕你误事。她说完便转身准备离开。我看那帮嬉闹的孩子,其实并不是觉得无聊,只是觉得自己老了,与他们一起有些不好意思。扭头看见珍和站在楼顶门口望着我,我料想她有事,于是拨了电话回公司。
什么事。挂掉公司电话,珍和呼着热气贴着我的肩。双手不停摩擦着。
明天去稻城采风,下个月杂志的主题。大概得去半个多月。我把手机收紧棉衣口袋里,吹过一阵风,我把脖子往围巾里缩。我就准备下楼去收拾行李了,你照看下这帮小毛孩吧。
明天啊,刚过完年就得走,真是…珍和抱怨着,我明白她内心越是空虚越想要依靠我时,就会表现出来,想粘着我,她吸吸鼻子。
工作嘛,我走了。说罢转身跑下楼,她没有叫住我。我没有给她机会叫住我,我想让她摆脱那种依恋,自己独立起来。
那时的黑夜,长在眼睛深处。
它们无所不在。
3.
这是怀素走后的第一个冬天,我还是爱着这个人,时时刻刻。我知道过往那些回忆,会是我着辈子最珍贵的财富,即使不堪,它却值得我去时时刻刻地想念。
珍和在那个有阳光的午后和我说,那是珍和失态后两个月,她开始慢慢进食,也开始和我说话,我们在楼顶晒太阳,她穿着那件米黄色碎花棉袄。我记得这是怀素送的。
没有什么是可以被彻底遗忘的,就算一些事被你遗忘,当有一天因为某些关联的事牵扯出来时,被你遗忘的那些事,就会声势浩大地涌现。你会更加深刻。我看她目中有空,脸色的安静的祥和。好像,当初反对你们的我,现在能够理解你们,茫茫人海里,两个人能遇见,能相爱,那已经足够。有些人,不能理解这种感情的深刻,就想要凭借自己的思想去拆散人家。现在想起来,真是暗自庆幸你们的感情足够坚定。人家的路由他们自己走,路上该出现什么人,该和什么样的人停留,这些都是由他们自己选择。我不会再去插上已脚耽误人家的。这是你说的。她没有看着我,看着天空,眼泪没有掉下来。
若你知道你的余生,你要怎样去生活。这是她第二次问我。
别再黑暗中哭泣,试着去爱。我第一次回答她。
4.
从稻城回来已经是三月中旬,开门的时候我看见珍和跟那个短发女孩坐在一起,她们嬉闹的笑声在我开门后瞬间停止。
珍和身上穿着一件米黄色碎花棉袄,她起身雀跃地来到我身边,好看吗,她送我的生日礼物。珍和拉着身边羞涩微笑的女孩,她的愉悦使我有些措手不及,我把她的生日忘记了,因为无目的地观望,我记住了哪个女孩的手背,绿色的淤青,猛然间我记起了与父亲一个病房的女孩,越来越肯定。
我是怀素。女孩走近我,用轻的透明的声音说,眼睛清秀直接地看着我,眼神似一抹皎洁的月光。
我记得那晚珍和与我同睡在一张床上,黑夜给我们明亮的眼睛。借着屋外路灯的照射,我看见白天在她脸上的愉悦已经隐退,两只凌晨一点的眼睛,看起来镇定至极。但我明白她内心的忐忑。若你知道你的余生,你要怎样去生活。像光线穿过黑暗的房屋,潮湿的空气混沌不安。我喜欢她,这一定得是个秘密吗。
绍然若揭。
我只觉得心里黯然,我不懂怎样去回答她,她应该找一个温柔的疼爱她的男人,而不是一个奄奄一息的女人。我当然反对,并且明白,纵使这样的恋爱被众人认同,与怀素一起的欢喜知足也是短暂而平凡的。
或许是友情,同情..不是爱情。这必将遭到非议。
你不必把你的想法强加的我身上。她把连转向我,逐渐在黑暗中适应的眼睛笃定般看着我,窗外的路灯微弱的光亮只投在她的眼睛里反射给我,灼灼发亮,使我确定她非常清醒。也许根本没有人是从一开始,就带着意义出生,大家可能都必须自己去发现,寻找,也许所谓的意义,暧昧而不确定,或许还很不安定,但是只要还活着,就会知道那个意义是谁,为了某个人,而活着。
也许是这样彼此被认知和感受的感情,她说的话使我仔细琢磨了一番才认定那层意思,有太多直觉,能明白她缩表达的意境,即使她不说,压抑的心情似乎能透过亲密的血缘传达。
我极力装作镇定,我不能与外人一样用异样的眼光去批判她,她是我的妹妹,我深知在她没有确定方向时彷徨而惊恐,她为没有着落的爱情已遭受内心的谴责。最原始的思想使她潜意识认为自己在谈一场与人家不一样的爱情,怕遭受旁人异样的眼神而像让这段爱情成为一个秘密,羞于这并非世俗眼里的爱情,她的内心已经狼狈不堪,我只能将这样的谴责放在心里,焦急不安,在脑子里酝酿着能够有力反驳她的话语。只是良久之后我发现已经次穷。内心竟然已经开始默默认同她的说法。
只是我明白,这样的妥协,大多源自于怀素。
反正她始终会死,她的生活并不是她表面所呈现的那样。
十月的黑夜总是花掉我大量煤黑色和墨绿色的颜料,客厅里的风铃被从开了半边窗户外吹进的风摇晃得叮咚作响。在我准备拧开第二瓶墨绿色颜料的时候,珍和终于回来,寒冷的风灌进房里,门被关上,我猜想是风吹的,因为动静很大。
姐。她叫我,声音有些疲惫。
嗯,外面很冷吧,风那么大。因为天气冷的缘故,那瓶颜料被我拧了很久才妥协般被我打开,我没有停下手中的活,甚至没有望向她。直到许久之后没听见她的肯定回答,我才疑惑扭头去看她,见她仰面躺在冰凉的地上,我慌忙跑过去。弥漫大雾的眼睛没有焦距地望着天花板,鼻子不停地翕动着。
靠在我肩上吧。我把她从客厅拉回她的卧房,让她的头抵着我的肩。才发现手掌上有多黑色的颜料,它们凝固起来,像一块干涸的田地。我的心便是如此。随后我的肩上湿润的一片,卧房里没有开灯,黑暗中我看不到她的脸。以至于我有些不安,她开始从啜泣变成嚎啕大哭,一时间我找不到任何语言去安慰她,我总是这样不善于去安慰人,那些温柔的语言总是躲藏的细腻的心里。我只是搂住她,轻拍着她的背。帮她擦拭眼泪。手上黑色的颜料遇到水开始融化,我起身想去洗净着肮脏的手,她反抓住我的手,颜料弄脏了她的手,侵染了她黑色的头发,与黑夜融合在一起。
我们从来都不能选择自己要爱上一个怎样的人,就像我经常会想,我与珍和会和一个怎样的人相爱,未果。这是我们不能控制的。
爱情有时荒诞,可仍有人去尝试,并且死而无憾。
2.
2009年小年夜,那时北京下着大雪,有些温暖并且酥软,我没有时间欣赏这不寻常,甚至没有觉得这雪有多么不寻常,地上,房檐上都是白色的雪,放眼望去,一片平川。没被雪覆盖住的地方就成为了那一带显眼的标记。我在地铁站等地铁。没有坐过地铁的时候我以为地铁是不用等的,对于等待我过于烦躁,却总是心安理得地让人家等待。工作了五年,坐了五年的的地铁,等了五年的地铁。和北京繁密的上班族一起在阴暗的远离地面吵杂的站台。即使这里阴暗,也会觉得温暖。我才发现原来“习惯”这个词,也可以子这个时候用在我身上。
等到地铁哐当驶来时,我开始惘然。我将起身到医院。
一个小时前,接到母亲的电话,说父亲阑尾炎需要做场手术,还在公司加班的我慌忙收拾东西到珍和的学校,那时她在补课,高三的学习让她们在过年之际也不能得当全身心的放松,而老师告诉我她没来学校,于是怀着愤怒和忐忑走出了学校。只是现下最担心的时父亲,他苦了大半生。尽管对我们严厉,我是心疼他的。这么想着,眼泪突然就涌了出来,车厢里陌生,陌生,一切都是陌生,这些陌生人看着我裸露出的心情,漠然地望着我,我羞愧地擦拭,像身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般羞愧。幸好已经到站,我狼狈地从站台跑出来。这样狼狈地跑了几分钟,终于到了医院。
雪白的墙,还有穿着老旧得白森森的白大褂医生,白色的棉签,白色的纱布。进了医院,我才知道原来有这样一处地方,及时和外部的世界一样雪白,但是没有风霜雨雪。我整理好凌乱的头发和衣服,站上电梯。
九楼,907房,402床。我已经确定好位置。
电梯里还有一个人,一个女人。她没有什么表情,看不出是欣喜或是忧伤,或者说,她并没有遇到什么可以让她高兴或是难过,又或者,她已经长期处于某种状态下,感情在意麻木,不过我更愿意相信前者。巧的是,她去的也是九楼。
我在拐弯过去的第三个房间找到额他们,出乎意料的是珍和也在,她装着一盆热水,给父亲擦手,鼻子被风吹得发红,大概刚来不久,母亲在削苹果,病友们在漫长的治疗中找寻消遣的方法。他们在我进来的时候齐刷刷看着我,为了不沉浸在尴尬中,我借口上厕所,转身的时候发现刚才在电梯里遇见的女人,我几乎是踏出电梯的门就把她给忘记,之前也没觉得还能遇见她。
医院这么大。
她在给404床的一个短发女孩打针,女孩面色有些潮红,嘴唇有些苍白,针管轻柔地送入女孩的手背,那只手背已经被打得淤青,女人的眼泪滚了出来,我终于看到了她的表情。而哪个女孩却在沉睡。
那时的我们在路途上盲目地行走着,不知道牵引不明白宽容。
父亲在除夕那夜就出院回家,他执意要到家中过年。医生确认着不会影响她的治疗后,母亲才喜滋滋地给他办了出院手续。父亲那那一年回了家。而那场大雪,从那一年下到了这一年。
大年初一。街道上荒芜得让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忙碌的节日里显得特别多余,多余到每个人都在亲戚家拜年的时候,我还在带着珍和在回家路上漫无目的地行走——刚到公司交画稿。因为父亲生病,亲戚们都跑来北京拜年,所以即使在呆在家里,忙忙碌碌的也只是那些亲戚。
下午三点空旷的马路透着一些荒凉,雪暂时停了,但仍旧湿润,积雪很厚,脚一浅一深地踩下去发出咔吱咔吱的声音。此刻的城市没有往日的车马喧嚣,亦无人潮涌动,单只的行人看起来越发的冷清,庞大并且寂寞。
倒是珍和,回家路上遇见了几个同学,她把身上带着的贺卡送给了她们,说笑着打闹了会儿,突然觉得自己是空落世间的过路者,格格不入。
呼吸着冰冷的空气,致使鼻腔有些疼痛,不过伴随这种疼痛而来的,是冬天寒冷的熟悉,这种感觉总能让我觉得见到一个久违的朋友那般亲切。身心就这样愉快起来。
在经过医院的时候,有个短发女孩叫住了珍和,她有些紧张和窘迫,珍和也没有从口袋里拿贺卡送她。她只是对着女孩微笑,好像两个刚认识的朋友。
她说,过年好。女孩也微笑,过年好。
无异于常的对话或举动总让我好奇心萌动,我打量起这个女孩,她穿着一条黑色的牛仔裤,可以用孱弱来形容她,短发前的刘海服服帖帖地付在额前,樱桃一样的眼睛,冷风灌进她单薄的身体,因为紧张而咬得发红的嘴唇不停地打着颤,她努力控制着自己不这样失态,看出她在我面前有些拘谨,不过是个可爱的女孩。
在下好这个结论后,女孩发现我在注视她,于是对我笑笑叫姐姐。我给了她一个微笑,这是惯性,我习惯用微笑敷衍陌生人。
你和爸妈说说,我和朋友去玩会儿,晚饭前回家。珍和拉住女孩的手,对我挥挥手示意我快回家去。
嗯。我转过身,我知道她没听见我的回答,因为她们已经走很远。
有时候我们会想不起来,一些长相熟悉的人是在哪里与他们邂逅,那个女孩,也是似乎很久之前就在哪里见过,只是那个点总是想不到,有时候人们会突然忘记一件事,努力回想却想不起来时,会变的焦躁不安,随后又会想出点什么事寻求慰藉,然后心情又变得好起来。因为到了家里看见一群人忙碌的身影和满屋的清香,烦恼的事情早已抛掷脑后。
正月十六,吃过晚饭,带着小外甥和一群说不出辈分的孩子到楼顶放烟火。大概所有提及烟火的形容,都是转瞬即逝。曾画过一幅浩大的烟火,看久了,就不觉得有多新鲜。孩子们拿着从大人荷包里“变”出来的漂亮烟火,他们兴奋地点燃。或许是过了那种年龄,觉得这个年和平常的日子无异,过不过年,日子都得照样过下去,只是孩子们不容易满足,即使让他们在三伏天拥有那些绚烂的烟火,他们还是觉得在寒冷的冬季玩会比较又气氛。
天气的问题吧。我把手插进风衣的口袋,才发现手机没在口袋,围巾上竖立的绒毛扫着鼻子有些痒,低着头看地上厚实的积雪,我的心和它们一样充实着。被孩子们点燃的烟火散发出黄色的光芒。他们欢笑着踩在雪地上,我对着那散放在冬夜里黄色的光芒吐了一口热气,吐团黄色的气体很快消逝在也空中。
带这些孩很无聊吧。珍和伸手递给我手机,我接过来,下意识看看屏幕,有六个公司的未接电话。本来不想上来吹冷风的,看你手机震个不停,怕你误事。她说完便转身准备离开。我看那帮嬉闹的孩子,其实并不是觉得无聊,只是觉得自己老了,与他们一起有些不好意思。扭头看见珍和站在楼顶门口望着我,我料想她有事,于是拨了电话回公司。
什么事。挂掉公司电话,珍和呼着热气贴着我的肩。双手不停摩擦着。
明天去稻城采风,下个月杂志的主题。大概得去半个多月。我把手机收紧棉衣口袋里,吹过一阵风,我把脖子往围巾里缩。我就准备下楼去收拾行李了,你照看下这帮小毛孩吧。
明天啊,刚过完年就得走,真是…珍和抱怨着,我明白她内心越是空虚越想要依靠我时,就会表现出来,想粘着我,她吸吸鼻子。
工作嘛,我走了。说罢转身跑下楼,她没有叫住我。我没有给她机会叫住我,我想让她摆脱那种依恋,自己独立起来。
那时的黑夜,长在眼睛深处。
它们无所不在。
3.
这是怀素走后的第一个冬天,我还是爱着这个人,时时刻刻。我知道过往那些回忆,会是我着辈子最珍贵的财富,即使不堪,它却值得我去时时刻刻地想念。
珍和在那个有阳光的午后和我说,那是珍和失态后两个月,她开始慢慢进食,也开始和我说话,我们在楼顶晒太阳,她穿着那件米黄色碎花棉袄。我记得这是怀素送的。
没有什么是可以被彻底遗忘的,就算一些事被你遗忘,当有一天因为某些关联的事牵扯出来时,被你遗忘的那些事,就会声势浩大地涌现。你会更加深刻。我看她目中有空,脸色的安静的祥和。好像,当初反对你们的我,现在能够理解你们,茫茫人海里,两个人能遇见,能相爱,那已经足够。有些人,不能理解这种感情的深刻,就想要凭借自己的思想去拆散人家。现在想起来,真是暗自庆幸你们的感情足够坚定。人家的路由他们自己走,路上该出现什么人,该和什么样的人停留,这些都是由他们自己选择。我不会再去插上已脚耽误人家的。这是你说的。她没有看着我,看着天空,眼泪没有掉下来。
若你知道你的余生,你要怎样去生活。这是她第二次问我。
别再黑暗中哭泣,试着去爱。我第一次回答她。
4.
从稻城回来已经是三月中旬,开门的时候我看见珍和跟那个短发女孩坐在一起,她们嬉闹的笑声在我开门后瞬间停止。
珍和身上穿着一件米黄色碎花棉袄,她起身雀跃地来到我身边,好看吗,她送我的生日礼物。珍和拉着身边羞涩微笑的女孩,她的愉悦使我有些措手不及,我把她的生日忘记了,因为无目的地观望,我记住了哪个女孩的手背,绿色的淤青,猛然间我记起了与父亲一个病房的女孩,越来越肯定。
我是怀素。女孩走近我,用轻的透明的声音说,眼睛清秀直接地看着我,眼神似一抹皎洁的月光。
我记得那晚珍和与我同睡在一张床上,黑夜给我们明亮的眼睛。借着屋外路灯的照射,我看见白天在她脸上的愉悦已经隐退,两只凌晨一点的眼睛,看起来镇定至极。但我明白她内心的忐忑。若你知道你的余生,你要怎样去生活。像光线穿过黑暗的房屋,潮湿的空气混沌不安。我喜欢她,这一定得是个秘密吗。
绍然若揭。
我只觉得心里黯然,我不懂怎样去回答她,她应该找一个温柔的疼爱她的男人,而不是一个奄奄一息的女人。我当然反对,并且明白,纵使这样的恋爱被众人认同,与怀素一起的欢喜知足也是短暂而平凡的。
或许是友情,同情..不是爱情。这必将遭到非议。
你不必把你的想法强加的我身上。她把连转向我,逐渐在黑暗中适应的眼睛笃定般看着我,窗外的路灯微弱的光亮只投在她的眼睛里反射给我,灼灼发亮,使我确定她非常清醒。也许根本没有人是从一开始,就带着意义出生,大家可能都必须自己去发现,寻找,也许所谓的意义,暧昧而不确定,或许还很不安定,但是只要还活着,就会知道那个意义是谁,为了某个人,而活着。
也许是这样彼此被认知和感受的感情,她说的话使我仔细琢磨了一番才认定那层意思,有太多直觉,能明白她缩表达的意境,即使她不说,压抑的心情似乎能透过亲密的血缘传达。
我极力装作镇定,我不能与外人一样用异样的眼光去批判她,她是我的妹妹,我深知在她没有确定方向时彷徨而惊恐,她为没有着落的爱情已遭受内心的谴责。最原始的思想使她潜意识认为自己在谈一场与人家不一样的爱情,怕遭受旁人异样的眼神而像让这段爱情成为一个秘密,羞于这并非世俗眼里的爱情,她的内心已经狼狈不堪,我只能将这样的谴责放在心里,焦急不安,在脑子里酝酿着能够有力反驳她的话语。只是良久之后我发现已经次穷。内心竟然已经开始默默认同她的说法。
只是我明白,这样的妥协,大多源自于怀素。
反正她始终会死,她的生活并不是她表面所呈现的那样。